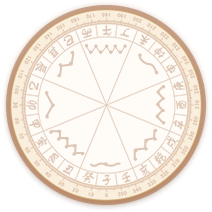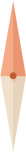萨尔浒之战为何失败?
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,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?
按《三朝辽事实录》里的记载,明军“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……阵亡……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……阵亡
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,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?
按《三朝辽事实录》里的记载,明军“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……阵亡……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……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,阵失马、骡、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,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。 ”
依据这则记载,萨尔浒之战,出征88,550名明军,阵亡46,180名,生还42,360名。
至于为啥明军会在萨尔浒大败,这个话题可以说是讨论烂了。
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是“分进合击”的四路明军遭遇“任他几路来,我只一路去”的后金军主力各个击破。但其实“分进合击”一种很常见的战术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术,是因为古代条件下,后勤运输手段有限,导致长距离后勤补给效率低,单位地理区域的补给输出也有一定限度的,故而组织十万级别的大规模进攻时,古人往往习惯把大军分开,以分担后勤的压力。
另外,参加过集体活动的读者肯定都会懂得,在道路宽度有限的情况下,大量人员一起移动,往往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人流,军队行军更是如此。比如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,普鲁士一个包含42,512人、13,802匹马、90门炮、1,385辆运输车的军,要占用43.5公里长的道路。这个在军事术语方面被叫做行军长径。而明代根据抗倭英雄戚继光的《纪效新书》十四卷本里记述, “ 路狭,挨次每一营鸳鸯阵双人行……前路宽一丈(约3.2米)……是二鸳鸯阵平行……前路约宽一丈之外……是三鸳鸯阵平行……前路约宽二丈……是四鸳鸯阵平行”。根据其记述推算,明军行军时单人的宽度大约在0.8米。另外,根据对近现代部队行军的研究,步兵行军期间前后的距离大约在1.5米左右,而骑兵则是2.5到3米左右。
萨尔浒之战中,明军总兵力为88,550人,朝鲜盟军的兵力为13,230人。这十多万步骑兵,就算按步兵6人、骑兵4人并排行军估算,明军行军长径将达到36公里以上,即前军已经走到萨尔浒、而后军尚在抚顺城刚出发。显然,这样的一字长蛇阵,即无法作战,也无法保证行进速度,更没法保证后勤供应。
而且,赫图阿拉周边群山环绕,山谷之间河流弯延,不利大军行军与展开。比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 “ 五岭特为险峻 ” ;兵部官员董承诏奏报 “ 越三关、逾五岭,闻其险隘之处,车不得方轨、马不得并驰 ”;扎喀关, “ 两山对峙,沟深峭陡,地势极为险要 ” 。
总之,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条件,明军要想执行攻击赫图阿拉、进剿后金这种外线作战任务,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,“没有合兵一处滚动前进的可能,即没必要也没有可以实现的地理环境(对于明军而言)”。
而这种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功的关键点,在于各支部队能够按照战前约定的时间,准时抵达应该抵达的地点,彼此呼应,相互掩护。
对此明军在出战前也进行了相关纪律的申明。比如违期逗留、观望不救援,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等纪律。但是即使三令五申,如果军队缺乏足够执行战术行动的能力,所有的纪律也就等于没说。
首先,成问题的是,这次明帝国出动八万八千人左右的明军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。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: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,各发精骑一万;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四处,各发精骑六千;川广、山陕、两直,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;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;永顺、保靖、石州各处土司兵、河东西土兵,数量二三千不等。很多明军因为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作战,求战之心不强,甚至“伏地哀号不愿出关”。
另外,明朝当时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担任大军主帅,而是由更高阶的文官调度全局。四路的率军总兵杜松、马林、刘綎、李如柏声望地位相仿、互不隶属。同时,明军为了弥补兵源短缺,不得不让一些有临阵脱逃劣迹的官兵也参与作战。比如,曾经对后金军望风而逃的抚安堡备御毛凤文、游击郑国良、白家堡备御周守廉、三岔儿堡备御左辅,都没有被严肃军纪,相反获准戴罪立功。而这种行为,其实本身就是对军事纪律的一种破坏。
士兵来自各地,彼此之间并不熟悉,士气不振;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础,更没有建立应有的指挥序列;军纪又没有得到。这样一支军队,要求他们在人生地不熟、地形复杂的敌占区,实行对时间、地点与行军速度要求很高的“分进合击”战术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而辽镇明军素有轻敌冒进的风气,现在军队里又有临阵脱逃不受处分的逃兵,其结果自然是“勇者独进,怯者独退”。
其实面对缺乏地利与人和,准备又不够充分的“分进合击”战术,其实领军的总兵也大都看出问题。比如马林表示,“王师当出万全,宜并兵一路,鼓行而前,执取罪人,倾其巢穴。”刘綎则提出,“地形未谙”,应推后进军的日期,到四五月份出兵为好。他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所组成的明军战力表达了不信任,希望能抽调川贵士兵两万,就能“独挡奴酋”。然而,辽东经略杨镐只答应让他调八千川兵,结果到出发前,刘綎麾下的川军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。而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,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,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,各营彼此又不熟悉,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,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。然而,当时明军的体制,武官只有列席议事资格,却没有军事决策权,只能被动执行文官的命令。结果,那几位总兵的意见与建议,全都被杨镐置之不理。
而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。之后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,只好推迟出兵日期。可大学士方从哲、兵部尚书黄嘉善、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大臣,却认为等待下去是耗费钱粮,于是一再催杨镐进兵。结果,明军就在准备不充分、内部问题重重的情况下,贸然开赴人生地不熟的辽东作战。也就是说,明军这次出兵,中国传统兵家所重视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全都存在问题!
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,明廷之所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,还选择分进合击战术并贸然进兵,其实主要源自于轻敌。明廷复制的是明宪宗时期“成化犁庭”的战略布局。但“世易时移”,此时明军所将要面对的则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、建立了政权,并且拥有极强军事指挥能力的后金开国之君、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。而且,后金政权拥有六万人级别的战兵,军队规模甚至能达到十万人。所以当初进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时很有效果的战略布局,很明显已经不适用了。但明廷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敌人的变化。那些朝廷大员,无视了一线军事主官的合理建议,还以剿匪的心态,将八万多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,推向了萨尔浒战场,去执行那个已经不适应时代的“分进合击”战术。而明军也在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下,将“分进合击”战术执行成了“分进独击”,结果给予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对其各个击破的机会。
相对于由于进行外线作战而困难重重,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,努尔哈赤的后金军由于处于内线作战,占据地利,后勤与行军压力要小得多。比如杜松以两天半的时间从沈阳抵达萨尔浒,要在崎岖山路上行军140多明代里(80多公里),而且还有浑河与苏子河两条河流的阻隔,最后还要面对坚固险要的界藩城。而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,军事地图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约66.7公里,即116明代里,并且地形一马平川、路途平坦。加之后金军多为骑兵和骑马步兵,机动能力要远高于明军。所以后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更好集中兵力,执行“任他几路来,我只一路去”的战术。
天时方面,17世纪时,北半球正处于寒冷周期,即著名的小冰河时期。而辽东本就是严寒之地。考虑到此次出征的明军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方,自然不可能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,战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。而后金军作为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渔猎民族,对于当时的严寒气候更具适应能力。
人和方面,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通过铁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势力。比如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因为保持亲明立场,结果被他幽禁折磨了两年多后,悲惨死去。(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,也有说法是被努尔哈赤秘密处死)。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一些亲信也被处死。
同时,后金军军纪严苛,作战时设有督战队,不守纪律者一律处死,“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,配朱箭,如有喧呼乱次,独进独退者,即以朱箭射之。战毕查检,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。”
另外,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营多年,根深蒂固,特别善于使用间谍和内应。当时,努尔哈赤号称“奸谍满辽阳”。明人评价为,“奴酋最狡,善用奸细”;“奴酋狡黠异常”,“间细广布”;“其用计最诡,用财最广,最用最密”;“奴最工间谍,所在内应”(《三朝辽事实录》)连《明神宗实录》也得承认,“辽人举动兼辽兵、辽马、辽饷,奴皆习知”,“奴酋狡诈机警,内地一举一动无不周知”。后金军攻陷抚顺、沈阳和辽阳等地,都大量依靠内应和间谍。比如,朝鲜史书《谍海君日记》记载:“奴贼攻城非其所长,(辽阳)陷入城堡,皆用计行间云。”
具体到萨尔浒之战,大量后金间谍使得明军“师期先泄”,也让后金军“得预为备”。而具体到作战中,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对明军实行各个击破战术,靠的也是战场情报上的单向透明。而相比之下,明军在萨尔浒战场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,这从杜松和马林部覆灭之后,刘綎部队仍浑然不觉就可见一般。
由此可见,以杜松部为代表的明军,在正式的战斗展开前,已经在“天时地利人和”诸多方面相对后金军都处于下风,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态势。此战还没开打,明军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……